花儿在,岁月在
家里养了几十盆花草,有客人来,总要引着展示一番。
喜欢花草的,能立即叫出“蝴蝶兰”“马蹄莲”,更多的分不清“绿萝”与“豆瓣绿”的不同,看不出“金鱼吊兰”与“冷水花”有啥不一样,出于礼貌会夸一句“你家的花可真多!”好奇的,会追问一句:“这个‘五彩千年木’开不开花?”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家张晓风讲过一个场景:五月,“极白、极矜持”的桐花满山遍野,每一块石头都因花罩而极尽温柔,强大的美有时令人虚脱。而当地一农妇对此却视而不见,且颇为诧异,“哪有花?”
作者看来,“花是树的一部分,树是山林地的一部分,山林地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是浑然大化的一部分。她(农妇)与花可以像山与云,相亲相融而不相知。”好一个“相亲相融而不相知”,正可谓“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日几回。唯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
喜欢花花草草的,自然女士居多。席慕蓉在其诗作中,会化身一朵荷花,讲述着女性最隐秘的情感——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风霜还不曾来侵蚀/秋雨还未滴落/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重门却已深锁/在芬芳的笑靥之后/谁人知我莲的心事。”
作家舒婷在随笔中甚至不掩矫情地自言自语:“我的前生,我们的前生可能是一株栀子花或水杉么?”她对家乡的榕树、三角梅、木棉的描述,满满的都是对家乡的款款深情、对生活的无限眷爱。
贪恋花草的男士也是有的,清代散文家沈复算一个。《浮生六记》“闲情记趣”卷,尽显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的艺术修养——“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文中对器皿与花材的匹配,对花木的修剪与品鉴,在今天看来,也算行家里手了。
在“迷恋植物芳名”的舒婷眼中,植物的名字体现了人类的观感、文明、智慧,充满想象力,“例如舞女兰、蛇目菊、灯笼花,因为它们的花貌像舞女,像毒艳媚人的蛇眼,像倒挂透红的灯笼。火鹤花是缩小版振翅欲飞的火鹤鸟,或者说火鹤鸟是放大的休憩凝立的火鹤花。”还有的花名“有时却是音乐:悬铃木、喇叭花,约钟柳;有时是唐宋辞赋:剪夏罗、美女樱、唐菖蒲;有时是乡间民谣:牵牛、落新妇、荷包牡丹、打破碗碗花;有时是异域舞姬:波斯菊、东瀛珊瑚、地中海蓝钟花……”
只是,这些芳名在如今的花卉市场上,越来越难得听到了。
好好的“白鹤芋”,多形象的名字,市场上叫卖,肯定会被换成讨喜的“一帆风顺”。类似的“步步高升”“鸿运当头”“幸福树”“发财树”之类的名字,被写在一张张红纸上,挂在花枝上招摇,一幅紧巴结主顾的样子。
曾买回家一盆“幸福树”,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她原来叫“菜豆树”或“豆角树”或“牛尾树”,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都带着田间地头的气息。这也怪不得摊贩,如果卖花只是个营生,那么卖“夏威夷竹”或“山茶花”,跟卖土豆或拖布,没啥大的区别。
摆弄花花草草,或许是图个怡情养性,或许还不止。就像每次读到那经典的诗句“让生命如夏花般绚烂”,总忍不住一种冲动——想抱一抱这美好的日子,哪怕几分钟前还在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琐事而愁眉不展。
花花草草给人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一种不息的生命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就像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句:小花绽放出蓓蕾,高喊着:“亲爱的世界啊,请不要凋零。”上帝对于庞大的王国逐渐心生厌恶,但从不厌恶那小小的花朵。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一位作家的话说得真好,借此收尾。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1105/2960779.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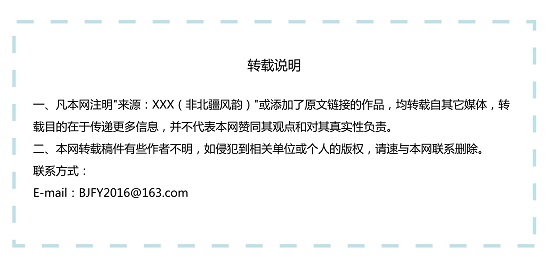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