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扇门背后没有秘密
——读艾丽丝·门罗自选集《传家之物》

《传家之物:艾丽丝·门罗自选集》[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李玉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传家之物》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的作品自选集。“自选”之取舍好恶,传递了作者自我评价的秘密:她的自我期许、美学理想,她试图赋予文学或被文学所赋予的写作意义。
门罗曾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小说家的创作方式和其看待世界的方式无不相关,正如门罗的美学理想所呈现的。《传家之物》收录的小说,多打乱正常的叙述线索,采用倒叙、插叙、平行结构、视角切换等叙事技巧,呈现事件本身的复杂和多义性。“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
于是读者看到,这些故事经由门罗之手的雕琢,在小说内部“众声喧哗”的表达之上,生活的多义性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小说世界中,没人能对生活做出最后的定论,同一事件在不同视角中来回切换——有趣的是,这既有助于看清事情的全貌,又让故事的面貌在越来越广阔的视角中渐渐失焦,“身在此山中”固然无法看清“庐山真面目”,但“远看成岭侧成峰”的困惑亦让“打捞真相”成为对生活徒劳的挣扎。门罗的小说中,生活最隐秘的内核是无法抵达的,每一个花蕊中都隐匿着秘密,秘密如同花香,只能感知,无法把握——然而门罗一开始并不会告知游览花园的目的,她向读者介绍植物的种类、花卉的形状,似乎秘密就隐匿在满园的艳丽之下,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之下往往触目惊心。
自选集中的开篇小说《好女人的爱情》,就遵循了这样的写作路数。故事开端讲到印有“验光师D.M.威伦斯”的验光师器材箱陈列在当地博物馆里,但门罗未就器材箱这一充满神秘气息的设置展开叙述,而是搁置悬念,开启小说的第二部分:星期六早晨,三个男孩在河滩游泳,冬天寒意刺骨,男孩在河中发现威伦斯先生的汽车,威伦斯死于车中。接下来的篇幅,同样没有马上解释威伦斯的死亡,作者再次搁置悬念,将时间线拉回到男孩们发现尸体之前——用不缓不急的语调叙述他们的游玩、男孩之间的情谊、日渐生长的男子汉气概,仿佛威伦斯的死只是整个平静乡村生活中微小的波澜而已。门罗曾自述:“真正的生活并不是线性的,符合逻辑的,它往往是发散的,真正的生活是碎片的集合。”

门罗没有紧接着描绘威伦斯先生的死在整个村庄引起的波动,甚至没有描绘男孩报案的经过,而是突然变换视角,开启了第三段讲述: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女看护伊妮德照顾患有肾衰竭的奎因太太,后者的丈夫鲁帕特曾是她的同班同学。奎因太太憎恨一切,“阳光,任何光线,现在都像噪音一样可憎……”她恨不得毁掉双手可及的一切。临死之前她向伊妮德吐露了秘密:威伦斯医生给她看眼疾时非礼了她,这一幕正好被鲁帕特撞见,被怒火吞噬的鲁帕特抓起威伦斯的头朝墙上撞去,没多久他就断了气。他们把他和车子一起推进了池塘中。没有人看见。没多久伊妮德就得了病。
开头的悬念在此刻得以揭示,无数碎片浮出水面,终于勉强拼出一幅稍显清晰的画面。谜底的揭示出于偶然,生活的真谛也于无意中闪现。迟迟来临的真相因此显得暧昧不清、真假难辨——伊妮德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报复的谎言?悬念似乎又暗示了另外的秘密:伊妮德对鲁帕特的感情。这份感情让她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她决定在河水中央询问鲁帕特,她甚至替他想好了退路——他可以把她推进河中,不留一丝痕迹。如果他悔恨,她将带他去自首。故事在伊妮德和鲁帕特前往池塘的路上戛然而止,开放式结尾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门罗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秘密并非小说的核心,或者说,它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与人物、故事相伴相生,如影随形——秘密是小说的底色,也是生活的底色,是人在抉择时刻微妙的张望,是一瞬间的善意或邪念。因而小说大篇幅的闲笔并非“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跑题,恰恰是对“平静又不平静的日常生活”的编织,将秘密包裹在三言两语的散淡人情中,如是当秘密被揭露时才显得险象环生。生活的真相总是突如其来,以至于真理和谬论往往难分你我。
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曾评论道,门罗的小说情节往往是次要的,“一切都是基于顿悟的时刻,突如其来的感悟……她与契诃夫一样着迷于时间,迷恋于人们在试图去延迟和阻止时间无情的前进步伐时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令人深感悲伤的无能为力。”
这种“悲伤的无能为力”,就是门罗在小说中致力描绘的人物的“命运感”,它有些类似于传统古希腊悲剧的母题,俄狄浦斯王无法摆脱的宿命,孙悟空无法跳脱的五指山,手掌中央指纹纠缠的曲线。
门罗感兴趣的是人物的 “命运感”而非“命运”,后者在意的是情节的发展、事件的结局,前者关注的是生命发生变化的瞬间与纹理,轨迹在拐点处的转折和变形,它们往往是非逻辑的,却在关键时刻给人以致命一击。如同《激情》中格蕾丝毫不犹豫地上了尼尔的车,她明知这一切是错的,但内心的渴望如飞蛾扑火般快乐。如同《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中萨比莎和伊迪丝的恶作剧,约翰娜用自己的爱孤注一掷,将恶作剧扭转成真实生活的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如“憎恨、友情、追求、爱情、婚姻”的排列组合,在偶然与不确定中闪烁。如同《荨麻》中突如其来的大雨,“我”和迈克在若干年后偶遇,被错误辨认的荨麻,是错位命运的隐喻。如同《逃离》中卡拉的优柔寡断,山羊弗洛拉的走失和回归,故事结尾卡拉想象中弗洛拉的头骨,揭示了她不愿直面的真相:丈夫带着残酷的爱……
它们是人物真切感受到“命运感”的时刻,这一时刻在小说微妙的肌理中得以升华,引导出关于生命的哲思,和浮出水面的真相一起直指人心。门罗的“命运感”让我们想到乔伊斯的“顿悟”,以及伍尔夫的 “重要时刻”。而在琢磨不定的“命运感”之下,门罗的小说世界里,没有哪扇门背后没有秘密。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927/2939055.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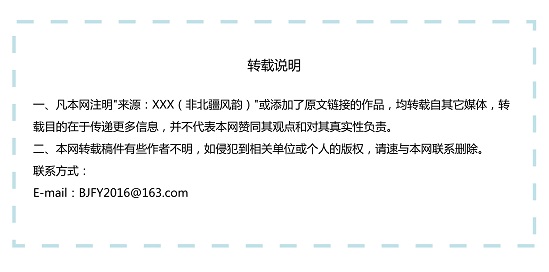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