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爱和被爱是我们应该争取的
列夫·托尔斯泰。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母亲老了。有一段时间,总是问自己的毛巾不知道被谁偷偷拿走了。反复多次,周大新才发现,这是母亲小脑萎缩的迹象,先是记不清事,后来认不出人,两年之后,母亲离开了人世。
谁能保证自己老了不会有这样的境遇?渐入老境,周大新也有一种恐惧感。他敏锐地感受着将近老年的生活,并知道这感受的珍贵。他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有类似的体验。他有种冲动要写作,通过文字反映老年人的生活。
这就是《天黑得很慢》的来历。养老、就医、再婚、儿女等等,小说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出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
近日,中华读书报专访作家周大新。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您生命中那些特殊的经历,使您受到很大的触动,作品是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周大新:过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切身经历,感受不是特别真切,难免写得轻,没有重量,只是在编故事上用力,很多东西没上升到哲学层面。自己经历的事情,才有真正深刻的体验,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结构上您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从陪护者的视角切入?
周大新:我住处的附近是玲珑公园,是夏季老人们纳凉的好去处,尤其黄昏时活动很多,打牌的下棋的推荐保健品的都有,我觉得,用黄昏结构我的故事应该很有意思。对老年人的观察总得有个身份,保姆的视角特别直接真切,医院和家庭护工可以直接接触老人身体,感受他们的精神问题。这个身份叙述起来最舒服、最便捷、容易被人接受。为了符合人物身份,我在叙述上没有太多修饰,语言比较直白,是为了真切地进入读者的脑子里。好处是,看不到的就不写,比如小说主人公萧成杉的女儿在美国的生活、萧成杉以前的生活都可以不讲,省却了很多叙述上的麻烦。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引用了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小说后半部分笑漾去吕梁山找道长求医问道,都是为了延缓衰老,您怎么看?尤其是道长所说的,通过吃奶的方式唤醒记忆,可有科学依据?
周大新:小说中既有技术也有幻术。小说前四章起类似拍惊堂木的作用,我用这个办法吸引观众。就像乡村里演戏,正戏开演之前要敲很长时间锣鼓。这里讲了很多技术,有些是忽悠的,有些是真实的,我相信科技发展会为延长生命带来福音。涉及“道”的部分,我是尽量符合道家传统。一位专门研究老年痴呆问题的专家看了后说,周大新的书不是科学著作,但有点道理。经过心理干预的病人会有好转。
中华读书报:写作上没有什么难度吧?写了四十多年,写作经验和技巧都非常成熟了。
周大新:每一部作品确定之后,怎么写都是痛苦的过程。最痛苦的是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叙事节奏、叙述样式,必须和自己不同也和别人不同。这是折磨人的。一旦确定叙述节奏,还要不断试验。这部小说几次开头都扔了。思考的时间很痛苦,搭架子很困难。
中华读书报:那写完《天黑得很慢》,您是否满意?
周大新:至少把我的思考说出来了。说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想会对老年人甚至对青年人都有意义。以后别人可能说得更好,但是写完这部小说我没有遗憾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两个女子,馨馨和笑漾,都遇人不淑。您对现代感情是否也持一些怀疑?
周大新:中国每年结婚的有九百多万人,离婚的有三百多万人,离婚率已经达到近三分之一。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乡村,一旦结婚是要过一辈子的,现在社会经济条件等各方面变化很大,家庭很不稳定,这也是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人口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应该保持在2.1%,我们国家是1.2%,这和婚姻的不安全感有关系。
曾经有一个朋友结婚,我送了他礼物,随后打电话问他收到礼物没有,他说已经离婚了——我确实对婚姻的质量有一些疑问。这也是我想写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原因。我把这些疑问呈现出来,希望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
中华读书报:笑漾经历着痛苦,但依然支撑自己义无反顾地履行对雇主的承诺,对老人不离不弃。您的作品中很多人物,如《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也承载了您的理想——是否也有理想主义情结?
周大新: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没有我就创造,我确实有理想主义情结,生活中恶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想给人们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
中华读书报:这种价值观,是受谁的影响?
周大新:列夫·托尔斯泰。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中华读书报:老鼠药在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分别用于笑漾和萧成杉的寻死。这个情节的设置,是否有重复之嫌?
周大新:我想不出不用鼠药的话,还用什么药来代替。别的药包括安眠药都是处方药,很难拿到。我尽量让读者忽略这个细节,它只是一个存在。
中华读书报:在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几乎是两年半一部的节奏匀速前进。
周大新:像我这样不善于说话的人,只能靠文字表达。除了写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也确实受到一些刺激,有些对人生、生命、自然的感受,想倾诉给读者,和他们交流,这样他们不需要像我一样经历那么多、过多少年之后才能悟到。
也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这种职业,应该对人类发展进步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生产精神产品,供大家享受。你可以呼吁大家珍视生命,重视生命的脆弱,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直接从理念上说大家可能不重视,通过小说,会强烈地打入脑子里。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创作状态如何?
周大新:小说越来越不好写,遭遇的痛苦越来越多。世界上年轻的作家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断在变化,不断创造,好多路都行不通了,要有自己的独创很难。这个行当,其实真不好干。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坚持了这么多年。
周大新:我是愿意做的,虽然苦,很有成就感。从事写作,真正快乐的时间很短。当你把一部书大的结构搭好,写作完成很快乐,刚拿到书,又要考虑下一步。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中华读书报:在这场马拉松的赛跑中,您有规划吗?
周大新:就像小说里的萧成杉,计划写三百万字,最后生病没能完成。进入老境不能做大规划,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必须小规划,这样才能不落空。将来可能写一写散文,把我的思考用散文的笔法写出来,篇幅短一些。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让自己激动起来再写。今天是一个崇尚青春的时代,报纸、杂志广告……都是年轻人的天下,我有点担心:年轻人会愿意看吗?
中华读书报:您是军旅作家,但是相关的军旅题材相对并不多。
周大新: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汉家女》,是关于南部战争。后来《战争传说》《预警》算是军事题材。相对来说军旅题材确实少了些,我对养育我的军队表示歉意。
军队是特殊集团,要鼓舞士气,打胜仗。作家又是不断发现问题的,对生活不满足才去写作。这是悖论。所以我宁愿把人物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像《曲终人在》那样的作品,所有人看了都会明白。我不止是写腐败,更是在写人生,如果真正读懂了,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官员,会有很多领悟。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安魂》《曲终人在》还是《天黑得很慢》,读完您的作品,总觉得悲凉。
周大新:这和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生命这个过程对人来说是个悲剧,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剧结尾:那么辛苦地长大、学习、劳动,最后是衰老、死亡——我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最亲的后代都不记得,他们活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追问自己,总觉得有种荒诞感。从乌有中来到乌有中去。这不是一个悲剧吗?我经常追问活着的意义。尽管人们不断为自己制造各种借口——有些观念可能不受年轻人喜欢,这是老作家应该注意的,甚至应该注意文字操作水平。
中华读书报: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文字操作水平?
周大新:大量的阅读。看今天一线的作家和外国作家,还要根据我们的文学传统和自己操作文本的习惯,不断地更新语言样式和风格,甚至包括使用文字的数量。
中华读书报:使用文字的数量?是您的发现?
周大新:我通过观察自己,看别人的小说也能发现,一个作家使用的文字其实不多,几千个字而已。用的字数越多,带来的寓意含量越大。人们常喜欢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表达。
中华读书报: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学习创新,但是从您的小说中很难发现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周大新:我早期读的还是传统的文学作品多,我们看到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不是原作。你要学的可能就是翻译家润色之后的作品。你写的是中国题材、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就得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再和现代的语言交集、交汇。
我自己觉得,学的那些东西和你写的东西不搭,就有一种防备心理,很警惕。所以当时我的写作“不先锋”,不太被关注。评论家陈骏涛曾写过评论,说我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中华读书报:那您看外国文学,借鉴的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吧?
周大新:我吸取的是他们对人生,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观察,观察的角度和态度,怎么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性的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叙述语言,叙述方式,把握住创新的原则就行。这是无限的。虽然难度会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有挑战,总能找到新的出口,开拓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最能考验作家创造力的。(舒晋瑜)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408/2819635.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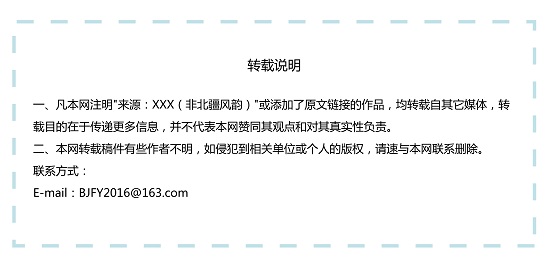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