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其身与佛
孔子作为中庸之道的创立者,凡事讲究个有进有退,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对此孟子有个很精辟的概括,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来的人将这句话所反映的情怀称作“孔颜气象”。
孔子的学说可以用“有为”二字概括。什么叫有为?主要包括学和行两个方面,将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学以致用”,即将我们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到指导社会的实践方面。在《论语》中,大约有六十四处讲到了“学”,七十二处讲到了“行”。例如讲“学”的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讲“行”的有:“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有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系统化并准确地揭示二者的关系,就构成了孔子学说“有为”的思想。
而孔子认为,学以致用的最好平台就是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本人“学而不厌”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教书先生去“诲人不倦”一辈子。他在周游列国十四年,六十八岁重返鲁国路过泰山时还作诗慨叹自己手无斧柯,对丛生乱长的荆棘一点办法也没有。意思是说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完成政治理想,而教书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

而就是这个“退而求其次”,表明孔子摆对了“达”和“穷”的关系。“达”是什么?达就是手执斧柯,从荆棘的丛生乱长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也就是所谓“为官一处,造福一方”。“穷”是什么?穷就是想当官而没有当上,或者当上了官又丢了官,包括辞官不做。一句话,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只能孤灯对坐,独守清贫。
如果世上的“达”和“穷”是静态的,孤立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然而达和穷是一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是井水不犯河水,又是相互依存转化的。特别是这个“转化”,揭示了“达”和“穷”的动态关系。相当初“夹谷之会”后,鲁国国君委任孔子代理国相,他面带喜色,三个月就将鲁国治理得四方之民咸来归附。但没想到的是,齐国害怕鲁国强大,用美女和宝马送给鲁定公来有意破坏鲁国国君与国相的关系。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孔子辞官不做,走上了周游列国十四年的漫长征程。
周游就周游吧,凭孔子之才,到哪个国家做个国相那也易如反掌,可他又坚持用仁道治国理政而不用军事手段强国富民,结果搞得各国国君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自己则“累累若丧家之犬”。
孔子的事例告诉我们,“达”和“穷”是可以转化的,孔子从“少时贫贱”转化成鲁国的国相,从鲁国的国相又转化成“丧家之犬”。这个转化是令人值得玩味的。我们经常说“心态要平衡”。面对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怎样才能在这坎坷、崎岖的起伏中保持心态的平衡?孔子和孟子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意思很明确,发达时就为国家、民族做一些大的贡献,困窘时就管好自己,虽然不能为社会做贡献,但也不能做危害社会的事情。这就叫“进退有据”“攻守自如”,这就叫“孔颜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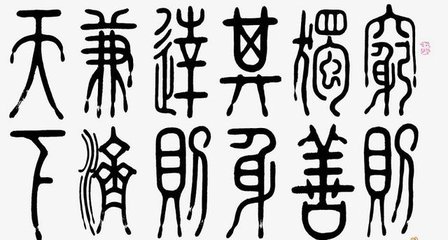
当我们搞清楚了“达”和“穷”的辩证关系后,再来看一下“独善其身”与“佛”的关系。
“佛”传入中国以来,和儒学进行了融合,可以说,佛教借助儒学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儒学通过佛教也得到了普及。既然二者可以融合,那它们就必然有相通之处,否则又怎么能谈到融合呢?笔者理解这个“佛”字就等于儒学中所说的仁爱向善。佛教说“人人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不就等于说“人人心中有仁善,人人都能变成仁善之人”?在这个关键之点上相通,那么两种学说的融合就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了。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样简单,毕竟是两种学说,在许多问题上观点还有差异的。
首先是对因果的理解有差异。儒家的因果讲的是现世报(当然它也不排除来世报,但不知来世是否存在,所以不强调这一点)。例如你为社会上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那么社会上的好人就会赞扬你,感恩你,回报你。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说你在发挥正能量,必然有正能量的人附和你。孔子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这样的话:“一乡之人都说你好,不符合客观实际;一乡之人都说你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只有一乡之好人说你好,一乡之坏人说你不好,你才是好人。”这里面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十分明了,就像毛泽东主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这个“争议”的关键是哪些人说他好,哪些人说他不好。搞清楚了这个关键问题,也就理清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佛教的因果关系偏重于现世与来世的递进,就是说现世修炼好了自己,那么来世就可以升天堂。有人在网上举了这样一个事例,说一个印度的贵族打死了一个印度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母很悲伤,但绝不会去报复,理由是孩子升天堂了,也是一件好事。印度的佛教徒在多次的灭国中已经沦为了贱民,而外来的侵略者都成了种姓的贵族。笔者曾经在资料中看到过,有许多印度年长的佛教徒身上一丝不挂地急匆匆奔向恒河,然后在恒河的水流中等死。他们把死看成了一件很紧要的事,急着要去天堂。儒家学者不反对人死后进天堂,但我们更重视现世生活,在现世中有所作为。
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它的主旨就是服务于社会。虽然孔子提倡社会和谐,但君子“和而不同”;虽然孔子提倡人性的向善,但如果你说井里有仁善, 我们也不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孔子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就是昭示我们人间有善恶,除了有绵羊,同时还有豺狼。所以,儒学倡导仁善,但并不忽视邪恶的存在,而且将提倡仁善看成是与邪恶斗争的目的,所以不排除用军事斗争来捍卫仁善。儒家更注重用财富来促使社会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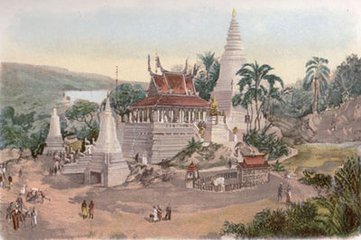
释迦牟尼的佛教在是树林里创立的。印度属于热带地区,人生活在树林里冻不死、饿不死,所以这个宗教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怕贫穷、不畏饥寒,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化缘,化缘后就在破庙里栖身。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来世的天堂里了,今生今世只有苦修,并且心安理得地忍受。所以原教旨主义的佛教徒不注重现世生活是否幸福,也不注重财富的多寡。因而有个现象:哪个地区宗教势力强大,哪个地区的科技就落后。为此,你不妨问一下原教旨主义的佛教徒,天堂里有家庭、民族和国家吗?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你就会意识到,那些和尚们在现世生活中也不主张家庭、民族、国家。这些看起来格局很高大,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格局总给我们以隐忧。起码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没有家庭、民族和国家,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
因此,我们呼吁,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原住民,希望更多地关注本土的宗教—儒教,而儒教被孔子改造成学说之后,完全趋于科学化,不仅可以做自己民族的指导思想,就是引导未来的世界潮流也是先进的理论。信奉佛教的中国人,要注意将佛的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吸收二者的长处,才能修出更好的人生。
佛教对于人性向善的教育意义很大,为社会的和谐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也能与儒家学说相融互补,是一种温和的宗教。起码说,它不会将汉民族吃猪肉看成就像狗吃屎那样恶心,也不会把无神论者看成是异教徒。就凭这一点,哪怕佛教与儒学有不相谐之处,我们也要求同存异,努力靠近,将儒与佛整合成一体。
【责任编辑:自由人】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