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
惠崇《春江晓景》 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是一首题画诗,是苏轼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为惠崇和尚的《春江晓景图》而作。惠崇是北宋初年一位著名的诗僧,也是一位出名的画家。据《图画见闻志》记载,他是福建建阳人,擅长鹅、鸭、雁、鹭等花鸟小品,所作“寒汀烟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道,世谓“惠崇小景”。据宋人葛立方诗话《韵语阳秋》介绍,当时的名流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与惠崇都有交往,对此“惠崇小景”也都极口称赞。王安石诗云:“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我最许。沙平水澹西江浦,凫雁静立交俦侣”。黄庭坚称赞曰:“惠崇笔下开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晖。梅影横斜人不见,鸳鸯相对浴红衣”。苏轼这是这首题画诗。“皆谓其其工小景也”(《韵语阳秋》)卷十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擅作小品的画家的《春江晓景》经过历史淘汰已鲜为人知,为这幅画所作的题画诗却声名大振,九百年来脍炙人口,吟诵不衰。要解释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只有从这首诗和这幅画的本身来找原因。
苏轼的这首七绝,把惠崇的“小景画”转化为“小景诗”,通过对早春江上典型景物的描绘,表现了春天给大自然带来的蓬勃生机,也给诗人带来了盎然的情趣。诗的首句“竹外桃花三两枝”,即扣住了早春这一特色。桃花,本来就是春天的象征,现在桃花只开三两枝,更显其春早,从布局上看,诗比画显得更为别致。诗人欲咏画面上的春江,却先写岸上竹外之桃花,这不但使画面显得很有层次,而且三两枝桃花点缀于青青翠竹之外,也显得疏淡雅致,更富有情韵。然后,诗人再用“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使画面由远景过渡到近景,也进入对主体的描绘。鸭生性爱水,一年四季多与水相伴,特别是寒冬过后坚冰初融,鸭群乍入春水更显得欢畅,因此在画面上用鸭戏于水来表现春江,这很典型,也显露出画家惠崇的独具慧眼,但从中着意点“水暖”,而且是“鸭先知”,这就是苏轼的功劳了。因为绘画毕竟是静态的,它只能用形体和色彩作用于人的视觉。画春水,无法直接表现水的温度;绘群鸭,也无法直接道出它们的知觉。因此,直接点出“水暖”,道出“鸭先知”,这是语言艺术的特色,也是苏诗的高明之处。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短短七字,使一幅静态无生命的画变成了一首有生命的诗。顺便提一下,有的选本把这幅画题写作《春江晚景》,这似乎不确,因为鸭子下水大都在早上,刚下水的鸭子会显得特别欢快,更何况是闲了一冬刚进入春江之时了。另外从诗中表现的情趣来看,这一派勃勃生机和到处洋溢着的活力,似乎与日暮之情也不协调。
诗的第三句再由主景回到旁景,这就是“蒌篙满地芦芽短”。蒌蒿,又叫白蒿,是一种春天生长出来的野草,芦芽,即芦苇的嫩芽,生于江边的浅滩之上。诗人在写了主体鸭戏之后又来写陪衬的蒌蒿和芦芽,这不光是为了使画面显得更加宽广和深邃,也不光是为了再次点出早春的季节特征和江边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引出第四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是一种淡水鱼,头圆口小,背褐腹白,有剧毒,但处理得好也是一种极难得的美味。河豚鱼正是在早春季节,由海入江,沿江上溯,俗称“抢上水”。苏诗所写“欲上时”,一方面是指早春河豚“抢上水”这一季节特征,另外还含有这时正是河豚肥美将上市之意。因为河豚以江边芦苇、蒌蒿为食,“河豚食蒿芦则肥”(王士祯《渔洋诗话》),现在既然是蒌蒿满地、芦芽短嫩,河豚必然肥美,上市亦即不远,食河豚的口腹之乐亦在眼前。由此看来,苏诗的最后一句比原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发挥了文学的想象功能,突破了绘画所无法突破的时空界限,道出了不属于画面但又与画面存在着必然联系的内容——河豚欲上时。诗人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使惠崇的画继续向前延伸,表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吸引入的生活情趣。前人总结题画诗的主要经验是“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郭熙《林泉高致》)。苏轼的这首题画诗正是与原画保持了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是这幅画的鉴赏和介绍,又是它的扩大和延伸,这是它在艺术成就上超越了原画,九百多年来脍炙人口、为人们吟诵不衰的主要原因。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附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一 宋·胡仔
《石林诗话》云:“欧公谓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阴最先得,方出时,一尾直千钱,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预以金瞰渔人未易致。二月后,日益多,一尾才百钱耳。柳絮时,人已不食,谓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恶之。而江西人方得食,盖河豚出於海,初与潮俱上,至春深,其类稍流入於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苕溪渔隐》曰: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时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语,似乎未稳”。
《韵语阳秋》卷十四 宋·葛立方
僧惠崇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故鲁直诗云“惠崇笔下开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晖。梅影横斜人不见,鸳鸯相对浴红衣”。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舒王诗云:“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我最许。沙平水澹西江浦,凫雁静立交俦侣”。皆谓其其工小景也。
《渔洋诗话》卷下 清·王士祯
萧山毛奇龄大可,生平绝不喜东坡诗,谓其词繁意尽,去风骚之义远。一日汪主事蛟门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句相难,谓“此等诗亦得云不佳耶?毛西河遽拂然曰:“鹅讵便后知耶?何独尊鸭也”!众为捧腹。
《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 清·钱泳
王辅嗣《易经·颐卦》“大象”注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古来已有此语,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当烹庖时,必以芦芽同煮则可解,坡公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盖谓此也。虾味甚鲜,其物是化生,蚂蚁、蝗虫之子一落水皆可变,煮熟时有不曲躬者不可食。绘鱼背脊有十二刺,应一年十二月,有闰则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类推,有中之者能杀人,惟橄榄汁可解。鸡味最鲜,不论雄雌,养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蟹者,深秋美品,与柿同食即死。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选一) 苏轼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以物喻人,托物咏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手法。屈原诗中的鸾鸟、凤凰,李白诗中的长鲸大、鹏,杜甫诗中的葵藿、佳人,都是诗人品格的外化,也都寄托着诗人所追求的理想。苏轼的这首绝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咏物,实际上是喻人。诗人借对直干凌空和根到九泉的桧的咏叹,来称赞友人王复光明磊落的为人,从而表现了诗人处世的态度和美学理想。王复,是当时杭州一位著名的医生,住候潮门外,家有园圃亭榭。这首诗是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过访王复园居见其所植双桧而作,共二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
全诗四句,基本上可分成两个部分。一、二两句咏叹桧的枝干,即人所能见到的部分;三、四两句赞颂桧的根部即隐蔽的部分。当然,桧的品格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是贯串其中的,对桧的枝干的咏歌,诗人主要突出两点:一是直干凌空,二是朴实无华,这两点也最能体现桧的品格。直干,是说它枝干挺拔,既无杨柳的婀娜之姿,也无桃杏的俯仰之态;凌空,表面上是在夸其材高大,实际上是赞它超凡脱俗,纵横于天地之间。“未要奇”则是桧品格的另一面:朴实无华,默默无闻,既不去争功邀宠,更不去炫奇斗艳,平日默默侧身于闲草幽花之间,只有在严酷的考验下才显出桧的本色来。诗人的这一层意思,在咏桧的第二首中表露得较为明显:“吴王池馆遍重城,闲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青盖”,用《晋书·陈训传》中的典故,指亡国败家之事。诗意是说在吴越王钱傚鼎盛时,宠柳娇花争奇斗艳,双桧隐没于其中默默无闻,一旦青盖入洛,吴越王降宋,花残柳败,只有双桧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迎来了太平盛世。孔子曾说:“岁寒知松柏之后凋”,松柏如此,桧的品格也是如此。也正因为桧具有上述的品格,所以人们对它是“凛然相对敢相欺”。凛然,是恭谨之状,这里既有作者对桧的敬佩,也有它本身凛然不可犯之态。清代方苞说游人一到雁宕山就会产生“严恭敬正之心”,其原因是由于雁宕山本身“笔立千仞,持身危正”,使人自然产生敬畏之心(《游雁宕山记》)。苏轼在这里说的“凛然相对敢相欺”,意思也在此。
下面两句,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把桧的品格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因为上面所咏叹的是桧的枝干,这是公开的,人所能见的一面;那未隐蔽的,人所见不到的根又如何呢?诗人称赞说“根到九泉无曲处”,这是夸张也是想象,因为桧根再长也无法扎到九泉;即使扎到九泉,诗人也无从得知。但诗人认为,桧的这种表里如一的品格,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世人也不知道,但总有人了解,总有人知道的,这就是蛰龙。蛰龙是潜于地下之龙,它对桧深到九泉的根的曲直当然是深知的了。
诗人一再称赞桧的正直不曲,表里如一,难道真的是在咏桧吗?不!他是在借物喻入,是要借桧的直干凌空来称赞王复的才干过人又刚正不阿,借桧的“未要奇”来称赞王复身处民间、平易待人,借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来称赞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据有关诗话记载,王复精于医道又能行侠仗义、以医救人又不图报,杭之人对他很是推崇,苏轼对他也很敬佩,曾为王复园中亭题名为“种德亭”。所以这首诗借咏王复园中之桧来称赞王复,表达诗人对他的敬佩之情,处处是在咏桧,处处是在誉人。
那么,这首诗的寓意是否仅止于此呢?“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弦外之音呢?有些评论家主张分析到此为止,不要再深下去了,因为苏轼为了这首诗,尤其是诗的后一句吃尽了苦头。据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御史舒宜等人诬陷被捕入狱后,狱吏曾把这首诗作为苏轼的主要罪证之一,在审问时追问“‘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讽刺?”幸亏苏轼回答的很巧妙,他引用了王安石的《偶题》:“山腰有水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王安石在这首诗中指责蟠龙不救苍生,却于山间吐泉,讥讽之意是很明显的,苏轼却说自己诗中的蛰龙就是王安石诗中的蟠龙。苏轼的罪名是以诗讽刺新法,而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苏轼把自己的诗与王安石的诗联系起来,狱吏投鼠忌器,只好作罢。另外,据《石林诗话》所载,当时的权贵确实是想借这两句诗给苏轼戴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置之于死地的。宰相王禹玉就曾向神宗进谗,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幸亏神宗还清楚,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予朕事?”苏轼才算保住了脑袋。诚然,说苏轼在这首诗中有不臣之心、反叛之意,这当然是穿凿附会,污蔑不实之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在诗中就没有寓意和寄托了,这只要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就可知道。在此之前,苏轼因对变法持不同看法引起了王安石等人的不满,但苏轼冒着顶撞权相甚至皇帝的风险,接连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进士策》等,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样更招来了王安石周围一些人的攻击。熙宁三年八月,侍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服丧期间不穿丧服,并假借出差派士卒来回做生意,苏轼在辩白不清的情况下只好要求离开京师。从以上的写作背景来看,苏轼在杭州所写的咏桧诗除了对王复为人品格的赞誉外,我认为此句还有以下以下两重内涵:一是诗人品格的自我表白。他为人光明磊落,不愿隐蔽自己的主张;他为人劲节堂堂,不因遭到排挤而改变初衷、委曲俯就。他相信自己的为人和主张,总会有人理解的。这些内涵通过对桧的品格的咏叹,暗暗地但又是明白无误地流露了出来。二是宰相王珪进谗之言并非无中生有,诗中的蛰龙确有暗示皇上之意,不过不是贬义而是褒义,暗指皇上为知己,对自己的赏识,而且不止是神宗皇帝,而是数代帝王。这在宋人的文史笔记和诗话中均有记载:
宋人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说,不仅是神宗,“而累朝圣主,(对苏轼皆)宠遇皆厚: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自凤翔签判满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耶!’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只是神宗对苏轼更加赏识:“神宗朝,以义变更科举法,上得其议,喜之,遂欲进用,以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补外”。除了“蛰龙事件”否决宰相的谗言外,在一次君臣对话中甚至认为苏轼超过李白,并排除层层干扰,直接下达手谕,将苏轼由监管黄州量移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默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庚溪诗话》卷上)
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苏轼黄州之贬后,神宗数次欲起用苏轼但遭朝臣干扰,最后不得已亲自下手诏的前后经过还有具体的叙述: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神宗元丰七年)
此诗虽写于“蛰龙事件”发生之前,但对神宗上述言行,苏轼不可不知,不可能没有感遇知己和危难中救助之情。只是仁宗、英宗尤其是神宗对自己赏识奖掖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心存感激。只是由于此诗要歌颂双桧的扎根身后,只能用蛰龙不能用“飞龙在天”而已。这同王安石《偶题》中“蟠龙”用典相同,只不过一是挖苦,一是讴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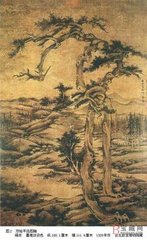
(元人四大家)吴镇《双桧平远图》
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神宗元丰七年 宋·李焘
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守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於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之句也。
《庚溪诗话》卷上 宋·陈岩肖
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自凤翔签判满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耶!”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神宗朝,以义变更科举法,上得其议,喜之,遂欲进用,以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补外。王党李定之徒,媒蘖浸润不止,遂坐诗文有讥讽,赴诏狱,欲置之死,赖上独庇之,得出,止置齐安。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於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时相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默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为南宫舍人,不数月,迁西掖,遂登翰苑。绍圣以后,熙丰诸臣当国,元祐诸臣例迁谪。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常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光尧太上皇帝朝,尽复轼官职,擢其孙符,自小官至尚书。
赠刘景文 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冬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一个严酷的形象。“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边塞的初冬;“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这是北国的苦寒。即使有人咏叹风雪中挺立的松柏,冰霜下怒放的红梅,也是以这个季节严酷的气候来反衬松柏,红梅的品格,而不是歌颂这个季节的本身。苏轼的《赠刘景文》却与此不同,诗人倒是怀着浓厚的生活情趣描绘了橙黄桔绿的初冬景象,并把此时誉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奋发进取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是写赠他的好友刘景文的。刘景文字季孙,开封祥符人,是北宋名将刘汉凝的孙子,曾任两浙兵马都监,又能诗能文。作者在任杭州知府时与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春渚纪闻》所载,苏轼在杭开浚西湖时曾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天天陪着苏轼在湖边巡查。苏轼调到颍州任太守后,还很怀念这段在杭结下的友谊,他在一首和刘景文的诗中写道:“万松岭上黄千叶,载酒年年踏松雪;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愁断绝。”这首《赠刘景文》也写于颍州任上,时为哲宗元祐六年(1091)。诗中借傲霜的菊花来暗示刘景文品格的高洁,并通过深秋、初冬生气盎然之景来暗勉友人不要气馁,在晚年取得更大成就。当然,从中也表现了诗人广泛的生活兴趣和那种积极乐观、奋发进取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诗人在景物的选取上既抓住了季节的典型特征又独具慧眼。一年四季各有自己的季节特征,所谓“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诗。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这是人们的一般看法,而苏轼却通过荷、菊、橙、桔等花木的变化和各具特色的形象来显示初冬小景,这就既有季节典型特征又别具一格。诗人围绕初冬的特征,选择了四种典型的花木,这四种花木又分成两种类型:初冬已凋残的——荷与菊,初冬正茂盛的——橙与桔,无论是凋残了的还是正茂盛的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充满顽强的生命力,使初冬变成一年之中最绚烂的季节。“荷尽”一句似写衰景,但“残菊”一句却作了及时的补救。这菊不是李清照笔下那满地堆积“憔悴损”的黄花,也不是柳永《乐章集》中那含愁飘零的衰菊,而是以自己的傲干对抗着风刀霜剑,以自己金色的花辦宣告严冬对生命摧残的失败。所以“残菊”一句为初冬的大地留下了生命搏斗的痕迹,也给全诗增添了内在的骨力。橙黄和桔绿则着力渲染了初冬的绚烂。这句是互文,即橙和桔皆是黄绿相间,由绿转黄之际。橙,又叫“黄果”或“广柑”,似桔但比桔大。就在菡萏香消、黄菊犹残,大地一片苍白的时候,橙和桔却以它青的枝,黄的果占断风情,在一片葱绿之中傲然挺立!于是,萧杀的初冬在诗人的笔下竟然变成了一个充满着生机、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难怪诗人要赞颂它是一年好景之所在了。诗人以荷、菊、橙、桔这几种极具典型性格的植物及其色彩来渲染初冬的绚烂和生机,就使这首绝句在构思上表现出一种独出心裁和别具一格的美!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另一个出色之处是它那丰富的含蕴。诗是要讲究含蕴的,所谓“语忌直,味忌浅,脉忌露”(刘熙载《艺概》)。遗憾的是由于宋人爱把才学和议论融入诗作,给宋诗(绝句也不例外)带来不少语直意露、形同说教的弊端,但苏轼这首诗绝无此病。他虽然有训戒之意、但却是通过鲜明的景物来暗中寄寓的。这种寓意不光表现在残菊的傲霜斗寒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橙黄桔绿的咏叹之中。屈原曾写过一首《桔颂》,歌颂桔“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等坚贞的内在品格和“青黄杂揉”、“绿叶素荣”等华美的外表。苏轼正是借《桔颂》中这种寓意来含蓄地表达对刘景文的赞赏:刘景文不但有霜菊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还有着橙桔的坚贞和华美。据有关笔记记载,刘景文虽是一位武官但又很有文才,“博学能诗,凛凛有英气”(《春渚纪闻》),为人又很清贫廉洁,据说“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游宦纪闻》)。因此,当时王安石、苏轼对他都很赏识。据《石林诗话》记载,刘景文初为饶州酒监,王安石时为江东提刑,有次到饶州来查问酒务,看到屏风上有首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询问后知是刘景文所作,大加叹赏,也不问酒务就升车而去,恰逢该郡无学官,王随即命刘景文兼摄学事,结果名声大噪,一郡皆惊。苏轼也曾把刘景文比作是三国时的陈元龙,并推荐他做过官。所以诗中提到傲霜的菊花和南国的橙桔,比附之意是很明显的。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诗人为什么偏偏喜爱初冬之景,写荷、写菊为什么又偏偏点出是枯荷和残菊?我们认为这与刘景文的遭遇有关,也与作者的生活观有关。刘景文虽是名将之后,乃父刘平又死于王事,于朝廷有功,但本人一生却坎坷多艰,从未显达。当苏轼知颍州时,刘已快六十岁了,曾寄一首诗给苏轼,慨叹老大无成,甚至对前途也丧失了信心。诗中写道;“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苏轼回了一首诗,题为《次韵刘景文见寄》,诗在回顾了两人的友谊后接着写道:“烈士家风安用此?书生习气未能无!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击唾壶。”诗中借曹操《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声和王敦高歌此诗击缺唾壶的豪宕之举来激励刘景文,要他发扬烈士家风,保持书生意气,不要叹息垂老无成,应该继续奋发进取。这首和诗写于元祐六年与《赠刘景文》的时间相近。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也就明白了诗人为什么偏偏喜爱一年中这个最后的季节,为什么着意点出“荷尽”和“残菊”了。当然,诗人之所以选择这个季节,选择这几种典型景物,并不单纯是为了暗中赞赏和激励刘景文,它与诗人自己的生活观也有紧密的关系。苏轼的生活兴趣非常广泛,他认为大自然的万物都有可观之处,问题在于你能否去发现它,欣赏它罢了。他的这种生活观在《超然台记》中表露得很明白:“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在这种生活观指导下,晴日的湖光他喜爱,雨中的山色他也喜爱;春江水暖,他觉得生机盎然,橙黄桔绿,他又觉得这是一年好景。所以不去叹息,不予偏废,尽情地欣赏、领略大自然为我们轮番展出的美景,把自己的生活情趣融合到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之中,这也是这首诗给我们的另一个方面的启示吧!

最是橙黄桔绿时
附
《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十 宋·胡仔
苕溪渔隐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子赡砌渗诗也。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
《巧对录》卷六 清·梁章钜
百文敏公〔龄〕屏藩滇中时,眷一伶儿名荷花者,色艺俱佳。越数载,公总制两广。荷花適至,仍令居珠江菊部中,而荷花马齿加增,颜发已秃。公戏之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盖公号菊溪,下句以自嘲也。
【责任编辑:自由人】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