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偶记
爱默生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行走的学者,在他的观念中,作家的创作行为,更多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憔悴。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的守望者。”
读普鲁斯的《影子》,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行人稀疏的街道,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他头上举着一支小火炬,在每盏路灯下停一下,引燃灯油,随即又像影子一样消失。”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其实就是一个点灯的人,他用文字守望着终极信念,在暗夜里为人们点燃灯光,照亮人们前行的路。
史铁生是一个文学信徒,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急功近利、商业炒作的文坛,他依然服从内心的信仰,从未偏离过对个体真实的坚守,他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高贵的信仰,当作精神家园的一种信念:“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阴暗,写作之最终的寻求即灵魂之最初的眺望。”
孤独是写作者的宿命,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几乎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所以桂冠诗人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在《记忆之书》里,奥斯特对“写作的孤独”做了一番精辟评论:“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或者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一间房内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钱理群认为:“你选择‘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宿命。”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1022/2951839.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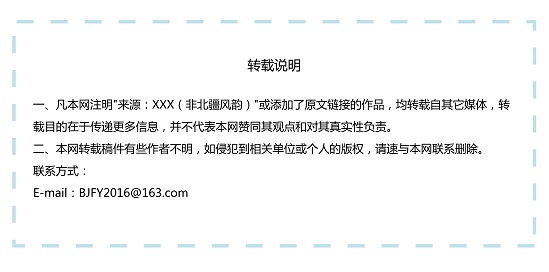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