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鞋垫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带领我们到邻村插秧,挽起裤腿、脱掉鞋子后,一个同学的鞋垫吸引了我,鞋垫是一道一道的各色布条拼成的,煞是好看,我忘了下田插秧,细细端详,直到同伴喊我。我问同学你的鞋垫是怎么做成的?同学自豪地说家有亲戚在服装厂,服装厂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料过一段时间就送给她家一包,她妈妈用缝纫机把这些边角料,做成了书包、鞋垫、门帘、椅垫。鞋垫的颜色单一,只用灰黑蓝绿,不算好看,最好看的是书包和门帘,赤橙黄绿青蓝紫,书包被她妹妹背走了,门帘做成横竖交错呈放射状的花纹。同学描述时,满脸是自豪和骄傲,低头看看我的鞋子,羞愧和懊恼涌上心头,鞋子黑不溜秋不说,鞋头咧了嘴后,补着一块黄色的补丁,疮痍满目,丑陋难看,鞋里还散发着异味。
家里贫困,兄弟姊妹多,母亲一年四季都在纳鞋底,做鞋,就这样,我们依然没有多余换洗的鞋,一双鞋子里面又臭又脏,穿到破得不能再补为止,白衬衣、蓝裤子、花裙子是不敢奢望的,就想着有多余的鞋子,有一双像同学那样的鞋垫。这个念头不可遏制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央求同学给我点碎布头,我让母亲给我做一双鞋垫,同学不给,说邻居和亲戚都向她妈妈索要,有的为了要布条,还用平素舍不得吃的鸡蛋换呢。
放学回到家吃完饭,我在屋里翻箱倒柜,希望找到点有用的布条,哪怕旧的也行。母亲粗朴笨拙的紫色木头箱子里,除了几件棉袄,什么也没有,针线筐里,放着几缕棉线和剪子、尺子、划粉之类,没有布,我卷起席子指望下面能压着点布条。母亲收工回来,看我恨不得掘地三尺,问我找什么,我跺着脚,眼里窝着泪水,不言不语,甩掉了鞋头有补丁的那只鞋子,狠狠地把席子“砰”的一声放了下来,屋里立刻尘土飞扬,母亲怒不可遏,拿起花瓶里的鸡毛掸子撵了出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光着一只脚跑了,躲在渠边队上的柴堆里后来竟然睡着了。
到了半夜,父亲和弟弟拿着手电筒把我找了出来,我冻得瑟瑟发抖,父亲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母亲看着我灰头土脸,长长地叹了口气,眼角红红的。她把那一只鞋递给我,鞋上的黄色补丁没了,补着一块和鞋一样颜色的补丁。
第二天早上到校后,同学悄悄拉了一下我的衣袖,示意我跟她出去,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布条塞给我说:“这些布条够做两双鞋垫的,你别跟别人说啊,说了还有人要呢。”我拿着布条,欣喜若狂,上课时一面假装听课,一面偷偷把布条按同一种颜色捋整齐,铅笔盒里有一根皮筋,我把布条用皮筋套上,盼望着快点放学,快点回到家。
终于放学了,回到家拿起母亲针线筐里的剪子、针,开始我的第一次手工制作,我把布条按照鞋样子,剪成长短不一,然后笨拙地穿针引线,经过几个小时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把这些布条连缀了起来,中间不小心还把指头扎了一下,血流不止,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用舌头把血舔舐掉,继续缝制,针线长短不一。眼看上学时间到了,我恋恋不舍把雏形鞋垫塞在枕头下,赶紧往学校跑去。
放学后,我继续未完成的工程,把连成的布条拿到墙后头,避开母亲,把鞋上的土拍掉,然后放在布上,用钢笔划了一个记号,依葫芦画瓢剪了下来,貌似像鞋垫了,可是周围丝丝缕缕,毛边子一点也不好看,正思谋怎么办,母亲过来拿干柴,看见我左撇子粗手笨脚的样子,接过针和剪子,依着我的鞋子大小,将四周修剪好,又用针线走了一道,顿时看着平整顺眼了,但此时只是一层布而已,回到屋里,母亲又东翻西找,找出一块白布,用铁勺打了浆子,把鞋垫粘在白布上面,我在旁边看。她说:“别着急,等晾干后,我再从中间横竖纳几道针线,明天早晨你上学时就有鞋垫了。”
半夜醒来上厕所时,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纳鞋垫,中指上的顶针亮闪闪的,母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小声说:“妈,快睡吧。”母亲说:“马上就完工了,你再睡一会吧。”她把被子给我拉了拉,盖住我的脚,继续聚精会神飞针走线。早晨醒来,枕头边放着一双鞋垫,我如获至宝,反复摩挲,针脚细密匀实,下地一看,两只鞋子并排放着,里面垫着鞋垫,大小合适,我把脚伸进去,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绵绵的、软软的,舒服极了。
到现在,一想到那双鞋垫,就仿佛看见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飞针走线,那股绵绵软软的舒服劲就涌上心头。(杨素凤)
原文链接:http://jswm.nmgnews.com.cn/system/2018/10/11/012580245.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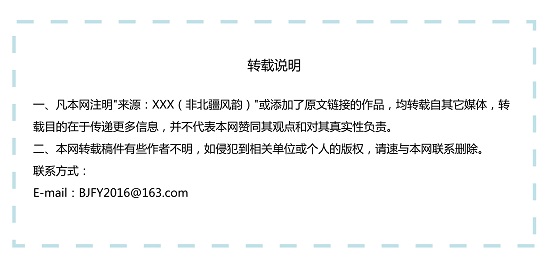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