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老家那地方
我的乡间老家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下的二龙眼河畔,叫红旗社,是个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社由中心屯和东山屯、南沟屯三个小屯组成,相互距离不到一里地。整个村子三面环山,山上长满各种各样的树木,丛林悠悠,山花烂漫。三个小屯中间是块偌大的草甸子,花草连片,流绿淌翠;银链般溪水弯来绕去,潺潺流淌,鱼跃鸭欢。四周的片片黑土地相连相近,庄稼的长势也是黑绿黑绿的,一切美得天然与平静,真是“棒打兔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景况。每每忆起乡间老家的自然景色,总是产生些许感怀,家乡人全都一心地保护着生态,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
那时候,红旗社里所有的人家住的都是土坯房、大草房或者马架子房,用柞树棵子、榛柴条子夹成院墙,规整自然,却空空荡荡。社里只有一台胶轮车、两台钢轴车和几台嘎嘎吱吱的老牛车,我经常听到车老板摇着鞭子哼唱的民谣:“小米饭,土豆汤,稀里糊涂混大荒,逛逛悠悠日子长……”
家乡的生活给我留下童年的记忆,那样真实、深刻,永远难忘。
小学毕业以后,我考进了县城里的初中,因为本县没有高中便又到外县的县城读高中,整整六年只有寒暑假才回到红旗社的家中。1969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四月,我背着行李再一次从城里回到红旗社的家里,就是扎扎实实的新农民了,美其名曰:回乡知青。这时候村子里有自行车或者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家也就是六七户,三户人家有缝纫机,看不见一个戴手表的人。男人若能有身趟子绒,女人如果穿上“的确良”,那便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时尚了。各家的日子谁也不比谁好多少,都是一样贫寒艰难,一样的苦不堪言。
每每夏锄铲地,望着二里地的垅头子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也想自己这个农民的身份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大家都在想这漫长的穷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不管怎样去想,谁都没放下手中的工具,依然没白没黑地耕耘着土地与岁月,中国农民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改革开放的洪流很快奔涌到红旗社这边远的小村,冬天里刮起了春风,人们笑了,那笑是从心灵深处冒出来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发展乡村经济,努力改善生活现状,黑土地上呈现出从没有过的大好景象。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家家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增施粪肥,改良土壤,从根本上增强地力。第三年,大多农户施行大豆满垅灌、谷子双苗眼、玉米埯种等科学的种植方法,耕耘方式也一下子改进了。农民的力量和智慧好像同时迸发出来,他们像绣花一样侍弄自己的土地与庄稼,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这年,农业丰收,全村卖粮30万斤,是历史性的大突破,红旗社头一次向国家交了这么多的粮食。老百姓兴奋地扭起大秧歌,放声欢唱:“鞭花飞,马蹄响,乡村送粮忙,家家户户喜洋洋……”转过年,又扩大黄豆、葵花、土豆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风调雨顺,块块地增产增收。因此,收入果真提高了,日子抬头了,农民笑眯眯地在家数钱了。
只要解放思想,就敢想敢闯敢干,就能迎来新局面。
村里请来有关的设计部门,对村舍进行全面设计,开始按新农村的规划进行建设了。三个自然小屯合并到一起,家家建房垒墙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村子正中修筑一条水泥大道,两旁等距离同方位地从北向南建起一排排砖瓦房屋,那个个院套与棵棵树木,给小村平添几分坚实的美丽。家家都有电视机、电脑、家用电器、手机、小四轮等农用机械,有的人家还有小汽车。观赏新村,想想以前的村落,谁能相信呢。

坚持改革开放,乡村致富奔小康的门路自然越来越宽广。村子里有的自愿组建合作社,有的搞土地流转,连片的土地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各种农作物年年都是好收成。随着养牛户、养羊户和养猪户的增多,积攒的农家肥上到地里,生产出的粮食自然是香饽饽了。与此同时,农民大胆地在村里或外地办淀粉厂、办加工企业、办装潢公司、办基建施工队、办运输、办大集……与农业有关或者无关的各种经营活跃起来,村里村外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到处都见到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我的小舅承包土地不久就与人联合办起了淀粉厂,不到三个月那几十间的大厂房就矗立在村子北面,成为红旗社一景。许家二小子聪明、能干,独闯县城办起了装潢公司,用农民的实在和纯朴赢得了信誉,生意兴隆,收入可观。那些脑瓜活的庄稼人,在种好土地的基础上,利用冬闲和农闲季节进城做小买卖、做家政服务、做小活维修、做卫生管理……他们凑到一起掰着手指一算,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呀。当今的中国农民,紧跟时代,走正道,迈大步,眼睛望出很远。
去年,我又一次回到乡间老家红旗社,正是七八月间,天气晴朗,和风送爽。发小国利和堂侄二宝子陪着我这走走那看看,快乐悠然。村里栋栋青堂瓦舍间的村路、门前道,皆是水泥铺筑,坚实、清洁、顺畅,如乡邻乡亲那样相连相通。路旁的路灯下,连续着树木、花草,姹紫嫣红,喷吐芬芳。顺路登上南山,见新栽的树林密密层层,婆娑摇动,下面野花竞艳,显得幽雅恬静。东山上的树丛之中,看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小鸟跳着奔跑,美丽的尾翼像船桨一样上下摆动。扑棱棱一声响动,一只野兔子从榛柴棵子里蹦出来,转动着滴溜溜的大眼睛,直竖着尖耳朵跑了。生态环境恢复了,山青水秀,家乡更美了。
傍晚,国利和二宝子又请来当年跟我一起种地的几位屯亲,餐桌放在院子里,摆好酒菜,大家一起吃着喝着,亲亲热热。酒菜过了三巡,大家都是激情满怀的样子,便扯着改革开放的话题谈唠起来。八十岁出头的崔老爷子端着酒杯说,现如今户户通电通广播电视通自来水,家家有大院套不愁吃穿,人人都入了合作医疗。四十年前谁敢想这些呀,我算赶上了好日子,多亏改革开放。国利说,四十年以前,咱村只有一个高中生,现在初中教育普及了,还有几个大学生呢。谈起外出打工和进城赚钱的话更是活跃,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又是一串新鲜事儿:刘家大小子在城里卖菜做小买卖,讲究诚信与服务都上报纸了;张家老姑娘在延吉开出租车,热心为人民服务,被评为先进;王家二儿子在大连造船企业当焊工,过年回来时领回的媳妇是个城里姑娘……
月亮升起来了,既圆又亮,泼下一地的银辉。村庄并没入睡,灯火闪烁,时有歌声飞来飞去。家乡人心情这样好,是因为谁都知道红旗社的明天会更加美好与神奇。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907/2927103.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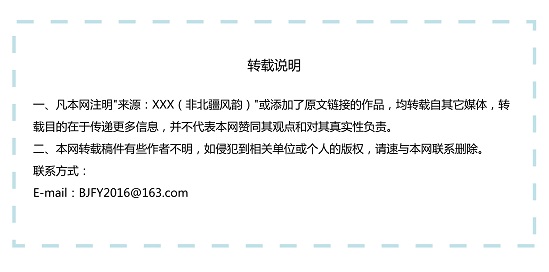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