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玻璃高足杯

玻璃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并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玻璃杯有什么特别。但如果放在几千年前,玻璃杯是否就显得有些神秘呢?若在一座古墓中突出了和现代玻璃杯造型、结构都颇为相似的玻璃杯,是否让人无限联想?是的,就在2003年的通辽市科左前旗吐尔基山辽墓中,出土了目前辽墓出土玻璃器中保存情况最为完好的一件。也就是今天要讲的“辽玻璃高足杯”,此杯时代为辽早期,口径9厘米,底径3.8厘米,通高12.5厘米,杯体透明微泛绿光。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内。
什么时候有的玻璃?
其实玻璃并不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玻璃的制作和加工。
埃及人和美索布达米亚人在公元前3400年至2500年发明了玻璃,用以制作首饰,并揉捏成小玻璃瓶。到了公元前1000年,古埃及人就掌握了玻璃吹制的工艺,能吹制出多种形状的玻璃产品。为了纪念古埃及人的这一发明,现代许多水晶玻璃作品上都有埃及人的头以及古罗马人和埃及人作战的图案。古罗马战败古埃及后,将古埃及战俘放在威尼斯岛上专做玻璃,由此玻璃制作技术传到意大利,以威尼斯玻璃为标志的玻璃制造技术达到了的鼎盛时期。大约16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工匠们开始挖掘和利用天然水晶,然而由于天然水晶硬度大、储量少,很难将它制作成器皿。因此,到17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玻璃制造商通过在石英砂溶液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由此发明了“人工水晶”,又称为水晶玻璃。人工水晶不仅克服了天然水晶的上述不足,而且其透明度高、折光性能好、厚重、耐切割,便于精雕细刻,成为玻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迎来了意大利玻璃的鼎盛时期。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工艺始于西周时期,在周原墓葬中曾出土过琉璃项链,扶风上宋北吕的本周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透明的琉璃。但那时的玻璃产量不多,技术略差且发展缓慢,而且长期保持自己固有的特点,即表面光泽晶润,“比之真玉,光不殊别”,但透明度无法与两河流域的琉璃相比,并且质地“虚脆不贞”,这主要是因为就化学成分和烧成温度这两个因素而言,我国古玻璃尚属于低温铅钡玻璃的缘故。
我国的玻璃制作发展
传统的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与推进,与古代炼丹家与道士烧炼珠玉的活动密切相关。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方士们就流行着“食金饮玉”可以长生的说法,所以炼丹术兴起后试炼珠玉(即玻璃)也就成为炼丹家们的活动之一。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进而“以药作珠,精耀如真”,玻璃制造技术有所发展。但从主观方面来讲,古玻璃出现以后,成为炼丹术的副产品,被道士们从人工冶炼珠玉的角度出发去总结和实践,没有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因而更谈不上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玻璃制作技术来。
受制作目的和技术的影响,传统玻璃制品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范围主要局限在礼器、装饰品以及冒充珍珠、宝石的珠子、戒指等物品,质地的轻脆易碎以及不耐高温,使得它很少被用作饮食器。由于透明度差,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制作光学玻璃了。
由于传统玻璃的这些局限,在西方玻璃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引起人们极大惊异,学者们视其为奇物异宝而加以记载。在《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两处玻璃的差异:“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蕃琉璃也。”玻璃制作技术传入以后,在中国的国土上也能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玻璃来,从此人们对玻璃就不以为奇了。此外,两宋时的大食诸国、清代早中期的西欧传教士都曾将玻璃制作技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玻璃制造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国外技术的传入及工匠的努力,我国人民最终掌握并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玻璃生产技术,并于明清时期登峰造极。
内蒙古地区的玻璃制作
位于山东省博山县发现的一处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内蒙古草原至今未发现玻璃制作遗址,说明草原当时没有形成专门的玻璃制造业,所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匈奴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没有像样的琉璃器。
到了汉代,匈奴与中原文化交流不断加强,通过战争、贸易及联姻等多种形式,将中原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草原,成为匈奴贵族们的生活用品,玻璃器也随之而来,西沟畔匈奴贵族妇女所戴的玻璃项饰与金饰片、玛瑙等饰品一起发现,组成一套华丽的首饰,成为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是北方草原的主体民族,在目前鲜卑文物中出土了较多的玻璃珠饰,以珠饰为主,且普遍存在于鲜卑墓群之中,说明玻璃珠饰成为鲜卑人较为普遍佩戴的饰品,而非如金银器一样只有贵族都会拥有。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其不一定产在本地,很可能是在与外界的交易中获得的。
辽代是西方玻璃器输入的重要时期,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和州回鹘便从西域来贡,进行贸易交往。天赞初年,波斯、大食等国先后朝贡于辽,到圣宗时期,这种交往更加频繁。所谓朝贡,实际上商业性质的往来是其主要目的。
到了金元时期,对外交流更加广泛和深远,在玻璃器的使用上也应更加普遍,但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代表这段时间的完整玻璃器在内蒙古地区尚未发现,仅有玻璃灯盏、簪等征集品,其来源有待考证。考其原因,除与蒙古族传统的秘葬习俗有关之外,蒙古军队连年征战,玻璃器易碎的特点也是其传世较少的原因。
辽玻璃高足杯 如何被出土?
在2002年夏秋时节,吐尔基山采石矿的工人们用推土机挖坑道时,在坑道的东半部,发现了一个三米多宽的石头堆,这些石头和吐尔基山的石头一样,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当时也没引起注意。到了秋天,坑道挖通,再也没有人想起石头堆的事。2003年新春伊始,为了赶在建筑工地开工之前备足石料,采石工地又开始炸石生产。
就在2003年“三八节”那天,工人们继续重复着以前的做法,在“乱石堆”中挖捡石块,在挖捡石块过程中,突然发现有淡红色的石头。凭他们的直觉,感觉到这种石头不是吐尔基山上的石头,抠下几块之后,发现里面的石头是经过人工摆放的,而且石块与石块之间有黑色胶泥粘着,进一步观察,有的石头上还用墨汁画着记号,当时有的工人怀疑:这是不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在这里修建的炸药库呀?
消息不胫而走,到3月10日,仅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吐尔基山发现“东西”的消息,很快传播出去,马上就来了好几拨“挖宝人”,他们都是来和采石矿的矿长谈价钱的。这里的矿长姓梁,身体强壮,是标准的蒙古族汉子。有的“挖宝人”问梁矿长:给多少钱才能让我们挖呀?有的还要和梁矿长一起分成。
3月10日清早,天还没亮,就有人敲梁矿长家的门,梁矿长出去一看,门口停着一辆
2020吉普车,来人对梁矿长说:听说这里发现了古墓,我们来看看,看你要多少钱才能让我们挖?这时梁矿长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马上回答:“不能让你们挖。”把这些人打发走之后,梁矿长操起电话,向公安局报告了情况。
公安局立刻联系了通辽市科尔沁博物馆历史部(现改称研究部)主任郝维彬。于2003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左右,工作小组来到了现场。根据现场观察,坑道东侧剖面上留下的墓道填土痕迹清晰,凭借以往的经验,郝维彬初步断定这是一座辽代墓葬,经目测(因为当时没带皮尺),墓道长超过
30米,墓葬埋藏深度10多米,墓室西墙的红色沙岩石条暴露在外,石条与石条之间用黑色胶泥黏合。天井处的部分石墙暴露在外,像似一个乱石堆,墓道的西壁北侧仅存少部分与石墙相接,南面的大部分已被推土机挖没了,仅见墓道中的回填土。从各种迹象判断,这个墓近期没有被盗过。但是搞过辽代考古的人都知道,辽墓十墓九空,这座墓葬早期是否被盗,在当时还是无法判断的。从墓葬暴露在外的迹象推断,这个墓是一座辽代中型偏大的贵族墓葬,墓主人地位较高,如果早期没有被盗,在这座墓葬中,将会有珍贵文物出土……
意义非凡,弥足珍贵
当然,辽玻璃高足杯就是在这座古墓中出土的,作为易碎的玻璃制品,能够被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已经是一种奇迹。同时也佐证了关于玻璃制作历史的文化脉络。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在辽代,精美的西方玻璃器成为契丹贵族之所爱,被视作豪华奢侈品,其价值远在黄金之上,上层社会人士斗富,往往用玻璃器皿来显示其高贵阔绰。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带把玻璃杯、长颈玻璃瓶、乳钉纹玻璃盘、乳钉纹带把玻璃瓶等器皿,从造型和工艺等多方面研究,并经科学检测,认为系从埃及、叙利亚、波斯、伊朗等国家的舶来之品。玻璃杯杯壁很薄,内有气泡,系采用无模吹制法制成。此件玻璃器器型,在伊斯兰地区也较为常见,反映了辽与西方频繁的经济往来。此种制作技术高超、器形完整的玻璃杯,在内蒙古地区的辽代墓葬中尚属首例,其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原文链接:http://www.hlnmg.com/prairie/archaeology/4093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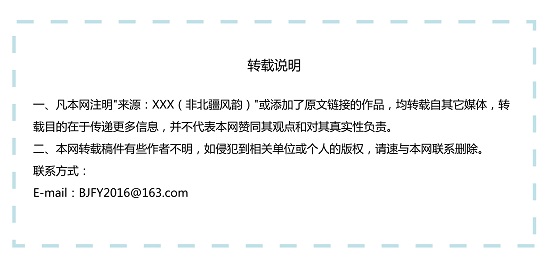
【责任编辑:尧日】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
蒙公网安备 15010202150610号